纽约,曼哈顿——清晨的阳光透过哥大巴特勒图书馆的拱形玻璃窗,洒在费若秋摊开的笔记本上,这位曾以凌厉攻势席卷法国击剑赛场的“东方剑客”,如今身着一件深灰色卫衣,安静地坐在阅览室角落,手边除了经济学文献,还有一本翻旧了的法语诗集,从巴黎的剑道馆到纽约的学术殿堂,费若秋的转型之路,如同他擅长的佩剑战术——看似突兀的转向,背后是精准的节奏把控与对时机的不懈追求。
“击剑是时间的艺术,求学也是”
费若秋的履历充满戏剧性:18岁赴法接受职业击剑训练,22岁斩获法国击剑联赛银牌,却在巅峰期悄然隐退,于去年秋季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。“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离开赛场,”他端起咖啡杯,指尖有一道浅色疤痕——那是长期握剑留下的印记,“击剑教会我的不仅是胜负,更是如何与时间博弈,每一次交锋都在十分之一秒内决定,但真正的决策可能源于一年前的某个训练细节。”
在法国南部蒙彼利埃的训练生涯中,费若秋以“预判能力”著称,他的教练曾评价:“他像下棋一样对待击剑,总能提前半步看穿对手的节奏。”这种思维模式被延续到学术领域,哥大经济系教授艾伦·米勒透露,费若秋在博弈论课程中展现出惊人的模式识别能力:“他提交的作业里,常能用数学模型模拟竞争策略,这显然与体育竞技的直觉有关。”
从剑道到书道:跨越山海的文化适应
适应期的挑战远超预期,最初三个月,语言障碍让费若秋在课堂讨论中沉默寡言。“法语和学术英语是两套系统,”他回忆道,“就像突然要求一个花剑选手改练重剑,动作逻辑全变了。”他的应对方式是极致的结构化学习:清晨六点背诵专业术语,课后追录播课至深夜,甚至将击剑训练中的“分阶段目标法”移植到学业中——例如第一周攻克论文框架,第二周专攻数据建模。
这种自律源于职业运动员的底色,在巴黎训练时,他每天清晨五点起床,对着镜子重复基本动作上千次。“肌肉记忆和知识记忆本质相通,”费若秋展示手机里密密麻麻的时间表,“只是现在我的‘对手’从赛场上的真人变成了德里达、凯恩斯和纳什。”

文化环境的切换同样需要柔韧度,巴黎的击剑俱乐部充满咖啡香与即兴对话,而哥大的学术圈更注重系统化论证,他曾因在研讨会中引用法国哲学家阿兰·巴迪欧的观点遭到质疑,“教授说我的论证‘太欧陆哲学’,不够实证主义。”这次经历让他意识到学术范式的差异,转而开始研究跨文化方法论,他的书架上并列摆放着《国富论》和法国诗人博纳富瓦的诗集,“两种思维模式像佩剑的攻防,需要找到平衡点。”
体育与学术的双向滋养
击剑训练并未因学业中断,费若秋每周三次前往纽约曼哈顿击剑中心,那里有他特意从法国订购的电动裁判器。“学术是脑力的延展,击剑是身体的对话,”他这样形容二者的关系,最近一次高校击剑联赛中,他带领哥大队伍逆转胜耶鲁,关键分正来自一次假动作诱敌后的突然进攻——这种策略与他正在研究的“信息不对称理论”意外契合。

“体育精神本质是面对不确定性,”费若秋分析道,“就像经济模型中的黑天鹅事件,你需要在有限信息下快速决策。”他的长期计划是结合体育产业与经济学,研究职业运动员的生涯规划模型。“传统体育管理过于依赖经验,我想用数据工具优化训练、转型等环节。”
“在纽约,每个人都是异乡人”
谈及身份认同,费若秋用“三重跨界”概括自己:中国出生的文化根基,法国塑造的竞技人格,美国开启的学术视野,他曾在除夕夜一边啃三明治一边准备期中考试,也曾在唐人街的爆竹声中与家人视频通话。“孤独感是必然的,”他坦言,“但击剑运动员早就习惯独自上场,重要的是把这种孤独转化为专注。”
他的宿舍墙上贴着一幅泛黄的法国地图,图钉标记着当年征战的城市:巴黎、里昂、图卢兹……旁边是一张哥大校园手绘平面图,图书馆和击剑馆被重点圈出。“地图不仅是空间坐标,更是时间轨迹,”费若秋说,“每次看到它们,我就想起自己如何从一条赛道跳转到另一条——这种跳跃本身已成一种连续性。”
窗外,哈德逊河上的渡轮拉响汽笛,费若秋合上笔记本,匆匆赶往下一节统计学课程,他的背影融入哥大熙攘的人群,步伐仍带着击剑运动员特有的轻盈与警觉,当被问及未来是否重返赛场,他微微一笑:“剑道的终点不一定是领奖台,也可以是思考的纵深,我的对手是无穷无尽的未知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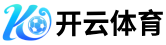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发布评论